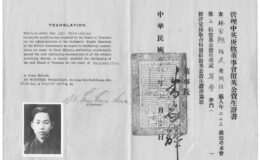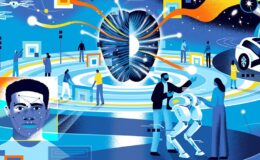那是我永远无法忘记的一个夜晚。
窗外的枫叶在暮色中轻轻摇曳,我正坐在餐桌前批改学生的作业。儿子坐在我对面,面前摊着一本图画书,手里捏着半个核桃。那是我们刚从超市买回来的,他第一次见到这种坚果,好奇地非要尝一尝。
“妈妈,这个好香啊。”他咬了一小口,眯着眼睛笑起来。我抬头看他,却发现他的笑容有些僵硬,脸颊泛起不自然的红晕。
在中国时,我从未见过这么多过敏的案例。记忆中的童年,孩子们随意分享着花生、瓜子,从没听说过谁会对坚果过敏。移民加拿大后,我才注意到超市里随处可见”不含坚果”的标识,学校里严格禁止带坚果类食品。这些细节曾让我觉得当地人过于谨慎,直到这个夜晚。
“怎么了?”我放下笔,凑近看他。他的嘴唇开始肿胀,像被蜜蜂蛰过一样。我的心猛地揪紧了,手指不自觉地颤抖起来。在那一瞬间,我想起小时候邻居家的孩子因为花生过敏被送进医院的情景。
“妈妈,我有点喘不过气……”儿子的声音变得沙哑,小手抓着脖子。我立刻抱起他冲向门口,连鞋都顾不上换。夜色中,我拦下一辆出租车,用蹩脚的英语告诉司机去医院。后视镜里,儿子的脸已经肿得变形,眼睛只剩下一条缝。
急诊室的玻璃门在夜色中泛着冷光。我抱着儿子冲进去,前台护士听到”food allergy”这个词,立刻指着地上的红色箭头:”Follow the red arrow! Go!”我的运动鞋在地板上发出急促的摩擦声,红色箭头在眼前不断延伸,像一条生命的通道。
还没走到尽头,几个医护人员已经推着担架车迎了上来。他们动作娴熟地将儿子转移到床上,我看着他小小的身体陷在白色的床单里,心都要碎了。抢救室里刺眼的灯光下,各种仪器发出规律的滴滴声,护士将肾上腺素注射进儿子的手臂。我紧紧攥着他的另一只手,感受着他微弱的脉搏。
“如果喉咙继续肿胀,我们可能需要做气管切开手术。”医生的话让我浑身发冷。我盯着监测仪上跳动的数字,祈祷着奇迹发生。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,儿子的呼吸渐渐平稳下来,肿胀也开始消退。直到凌晨,医生才确认他已经脱离危险。
我瘫坐在病床边的椅子上,这才想起要给丈夫打电话。窗外的天色已经泛白,枫叶在晨光中轻轻摇曳,就像四个小时前一样。但我知道,从今以后,每次看到枫叶,我都会想起这个惊魂之夜,想起那条救命的红色箭头。
护士送来一杯温水,我这才发现自己浑身都在发抖。儿子还在沉睡,小手依然紧紧抓着我的手指。我轻轻抚摸他的额头,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。在这个陌生的国度,我们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东西,比如如何识别过敏原,如何在紧急情况下保护自己。
但此刻,我只想感谢那条红色的箭头,感谢那些素不相识却全力以赴的医护人员。在这个寒冷的异国他乡,是他们让我感受到了最温暖的善意。我望着窗外渐渐亮起的天空,想起在中国的日子,那时的我从未想过,一颗小小的核桃竟能带来如此大的危险。这种认知的差异,或许正是移民生活中最需要适应的部分之一。